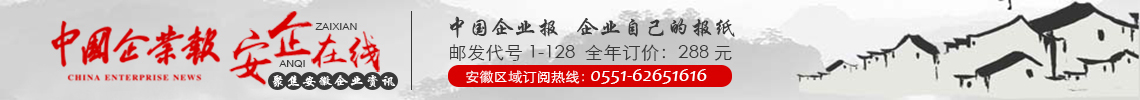郑万全(64):毒草与香花的辩思
时间:2025-10-11 14:46来源:中国企业报看安徽 作者:明骅英
作者:明骅英 传统语境中,香花与毒草的标签早已超越植物本身的属性,成为道德评判的符号。人们歌颂香花的芬芳艳丽,便赋予其美好善良的象征意义;忌惮毒草的潜在危害,便将其与邪恶危险画上等号。郑万全却尖锐地指出,这种认知存在根本偏差:毒草未必有害,香花未必有益。 还原自然的本真价值 古今中外,人们总爱用香花象征美好,以毒草隐喻邪恶。这种固化的认知
作者:明骅英

传统语境中,“香花”与“毒草”的标签早已超越植物本身的属性,成为道德评判的符号。人们歌颂香花的芬芳艳丽,便赋予其“美好”“善良”的象征意义;忌惮毒草的潜在危害,便将其与“邪恶”“危险”画上等号。郑万全却尖锐地指出,这种认知存在根本偏差:毒草未必有害,香花未必有益。
还原自然的本真价值
古今中外,人们总爱用“香花”象征美好,以“毒草”隐喻邪恶。这种固化的认知如同无形的枷锁,禁锢着我们对自然万物的真实理解。芜湖郑万全医院专职医生郑万全,以其独特的跨界视角,在关于“毒草与香花”的思辨中,撕开了这层被历史迷雾笼罩的认知薄膜——他直言“毒草是香草,香草是毒草”,大胆颠覆了延续千年的隐喻体系,为我们带来一场深刻的认知革新。
从中医药的视角看,许多被贴上“毒草”标签的植物,恰恰是治病救人的良药。附子有剧毒,却能回阳救逆,是治疗危重症的“救命草”;曼陀罗含莨菪碱,适量使用可止痛解痉,在麻醉史上曾发挥关键作用。
反观香花,虽能带来视觉与嗅觉的愉悦,其实际功效却远不及毒草——除少数可入药或提取香料外,多数香花的价值仅停留在观赏层面。人类可以离开香花的点缀,却无法忽视毒草在防治疾病中的重要作用。
这种对自然属性的还原,揭示了一个本质问题:将道德评判强加于植物,本身就是人类认知的自我局限。

善恶存乎于心而非物本身
郑万全进一步提出:“毒草成为毒品是人类管理和教育的错,不是毒草本身的错。”这句话直指药物伦理的核心——物质本身并无绝对的善恶之分,其价值取决于人类的使用方式。
以吗啡为例,它从罂粟中提取,既可作为强效镇痛药,缓解晚期癌症患者的剧痛,也能被滥用为摧毁意志的毒品。同样的物质,在规范医疗中是减轻痛苦的福音,在失控滥用中是毁灭人生的恶魔。
这恰恰印证了“善恶存乎于心”的哲理:问题不在“毒草”本身,而在人类能否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与理性的使用认知。当前全球推行的药物管控政策,其核心正是通过严格规范、教育引导,让“毒草”的疗愈价值得到发挥,同时遏制其潜在危害。
对于中医药而言,这一观点更具现实意义——许多传统药材因“有毒”被误解,唯有通过科学研究明确其药性、规范其用法,才能让古老的智慧在当代焕发活力。

从临床到诗性的双重见证
郑万全的特殊之处,在于他兼具诗人的洞察力与医生的专业性。作为诊疗人次吉尼斯纪录的申报者,他在数十年的临床实践中,见证了无数“毒草”的疗愈力量;而作为诗人,他又能以敏锐的感知,捕捉到传统认知中的矛盾与荒诞。这种跨界身份,让他的思考既扎根于实践土壤,又超越了学科局限。
当他写下“把坏人比作毒草是历史的错”时,其背后是对“毒草”被污名化的深刻反思——邪恶的人或事,本质上是违背人性的“丛林法则”的产物,更应被比作“魔鬼”,而非承担着疗愈使命的毒草。
这种区分,不仅是对植物的正名,更是对人性的深刻观照。他的诗歌因此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创作,成为融合科学认知与人文反思的跨界文本,其说服力不仅来自逻辑的严谨,更来自实践的见证。
在中医药振兴与批判性思维普及的今天,郑万全的思考无疑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。它提醒我们:看待事物不应被固有标签束缚,而应回归本质;利用资源不应被恐惧左右,而应依靠科学。
毒草与香花的辩证,最终指向的是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——唯有破除二元对立的思维,以理性认知替代偏见,以规范管理替代放任,才能真正读懂自然的馈赠,让每一种存在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。这,或许就是这场认知革命最珍贵的启示。
相关文章
- 12-23刘庄煤矿纪委:“清风家苑”涵养清廉政风
- 02-29尹同跃的“38军”,捷途究竟有多硬核?
- 10-23涡北选煤厂突出创新驱动决胜年度目标
- 04-05邹庄煤矿获安徽省“煤矿安全生产先进单位”称
- 05-14怀宁农商行“百行进万企”为小微企业注金融活
- 09-11攻坚克难合肥市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
- 05-21中国·活海欢乐水世界第二季盛大开园
- 07-01合肥市瑶海区小学生假日安全课
- 03-07桃园矿“两会”春风鼓干劲
- 03-28怀宁县春播种子建有“户口簿”